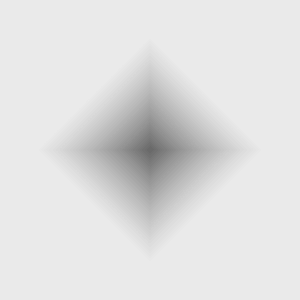熱門話題
#
Bonk 生態迷因幣展現強韌勢頭
#
有消息稱 Pump.fun 計劃 40 億估值發幣,引發市場猜測
#
Solana 新代幣發射平臺 Boop.Fun 風頭正勁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令人不安的想法,這個想法滑而難以捉摸。你有沒有注意到,宗教虛偽和“覺醒”激進主義,儘管表面上看似不同,卻有著令人不安的共同缺陷?在它們的核心,似乎都在同一個根本錯誤上絆倒:將表面的美德誤認為真正的美德。這不僅僅是一個隨意的觀察,而是揭示了人類行為、信仰體系以及在當今世界追求道德地位的更深層次的模式。
正如羅布·亨德森深刻指出的,“奢侈信仰”是精英們為了顯示道德優越而採納的思想,而不承擔個人成本。這些信仰,無論是披上信仰或社會正義的外衣,都優先考慮地位而非實質,注重表象而非影響。宗教虛偽者在講壇上宣揚虔誠,同時利用他們的地位謀取權力或利益,就像“覺醒”激進主義者倡導正義,但有時卻推動那些使他們聲稱要提升的社區感到疏離的政策。考慮一下2024年美國大選:長期以來被認為是進步理想堡壘的民主黨據點,看到意外的共和黨增長,特別是在工人階級和少數族裔社區。為什麼?許多人覺得“進步”的言辭在解決他們的生活現實、經濟困境、犯罪或文化脫節時顯得空洞。諷刺的是:既自以為是的傳教士和表演性的激進主義者都像戴著面具一樣將他們的信仰與外表混淆,混淆了表象與有意義的變化。
這種認知虛偽(行動背叛言辭)源於一個更深層次的錯誤:將外表與現實等同起來。“覺醒”一詞,最初源於對系統性不公的意識,已被武器化為貶義詞,成為某些人的地位象徵,而對其他人則是一個 caricature。社交媒體放大了這一點,將複雜的運動簡化為標籤和熱議。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62%的美國人認為社交媒體使政治討論變得更具表演性而非生產性,用戶往往優先考慮病毒式傳播的影響而非實質性對話。同樣,宗教虛偽在道德姿態(例如,公開的虔誠表現)掩蓋個人責任的環境中蓬勃發展。這兩種情況揭示了空洞姿態的循環:講道並未轉化為同情,或激進主義未能以切實的方式解決貧困或不平等等系性問題。
但有趣的是……也是令人不安的。這種共同缺陷不僅僅關乎個人;它關乎獎勵表演而非真實性的系統。在宗教機構中,領導者通過展現聖潔來獲得影響力,即使他們的行為與他們的言辭相悖。在“覺醒”空間中,影響力來自於與“正確”事業的信號一致,即使這些事業與邊緣化群體的需求脫節。結果是?一個道德市場,其中美德是貨幣,而最響亮的聲音往往失去的最少。亨德森的“奢侈信仰”框架在這裡尤其令人震驚:精英們可以主張削減警察經費或開放邊界,因為他們生活在封閉社區或將孩子送入私立學校。與此同時,他們聲稱代表的工人階級社區卻承受著意想不到的後果。
那麼,替代方案是什麼?如果表演性的美德是問題,那麼根植於謙卑和責任感的真正影響必須是答案。但這需要面對不舒服的真相。對於宗教信徒來說,這意味著優先考慮生活信仰而非公開展示。對於激進主義者來說,這意味著傾聽他們所服務的社區,而不是從象牙塔中講道。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這意味著質疑我們自己的動機:我們是在尋求真理,還是在追逐被視為“好人”的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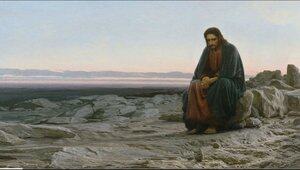
17.31K
熱門
排行
收藏